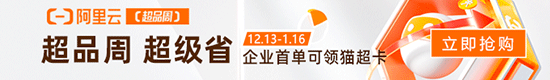我的离开也是爱 电视剧《不要离开我》
今年3月末,漫威宇宙中超级反派“征服者康”的扮演者乔纳森·梅杰斯(Jonathan Majors)因涉嫌殴打女友被捕。据外媒报道,两人当晚从位于布鲁克林的一家酒吧乘出租车回家,女方看到陌生女子给乔纳森发信息后与其对峙,争执中乔纳森不仅给了女方一巴掌,还试图勒住她的脖子。次日清晨,女方向当地警方报案,经验伤确认受害者耳后及面部有多处瘀痕,纽约警方也以殴打等罪名对乔纳森实施逮捕。
乔纳森·梅杰斯(Jonathan Majors)因涉嫌殴打女友被捕。图片来源:CNN官网。
案情至此似乎已然明朗,但事发后不久却急转直下。先是监禁中乔纳森否认使用暴力,并称其律师团队正在搜集证据以证其清白,随后,乔纳森的律师向媒体透露,涉案女方还提交了撤案说明。目前,乔纳森本人已经交保获释,具体案情仍在调查当中。一场惊动各界的“亲密伴侣施暴案”竟以这样的方式潦草收场。然而,这样的情节在类似案件中却并不少见。
跳出乔纳森一案,我们会发现,家暴案中受害方撤回指控证词这一行为往往是整个案情中最容易被人误解的部分。不少受害者会选择在公开场合与配偶站在一起,将看似能够提供援助的家人、朋友、律师、警察通通拒之门外。这些还只是经过立案后进入公众视野的事件,每年还有许许多多的家暴行为发生在一道道虚掩的家门之后,这种暴力不同于其他犯罪,大多数时候它是被遮盖的,甚至连最亲密的家人朋友也无从得知。
于是有疑惑声涌来:“为什么受害者还不离开”?
在深入走访美国多起家暴案件前,美国记者蕾切尔·路易丝·斯奈德也有相似的困惑。2000年初,美国蒙大拿州曾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致死案。名为洛奇的男子在开枪击杀妻子米歇尔后,杀死了家中的两个孩子,随后泼洒汽油点燃了房屋,最终回到地下室自杀。据称,米歇尔生前曾报案称遭到家暴,并申请过对丈夫实施限制令,但没过多久她便张皇冲进检察官办公室撤回了所有指控。看似反复无常的行为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走访中,斯奈德联系了遇害者的多位亲友,并通过一卷录像带逐渐还原出案情上升的经过。她尝试揭开捆缚受害者的多种力量,剖析施暴一方的心理动因,并与那些在反家暴前线战斗的先行者对话,寻找在逮捕和监禁之外其他可能的应对方式。多方辗转中,她渐渐意识到,我们对家暴本身其实知之甚少,这也是为什么在“反家暴”口号被一遍遍提及的今天,社会层面在反家暴的具体实践中依然进展有限。
斯奈德将她对家暴问题的诊断与防治思考写进了《看不见的伤痕》。回过头看,这本书所记录的绝不只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亲密关系中的恐怖主义与暴力模式无关国界,它真实地存在于一对对具体的关系中。当有一天,我们的问题不再是“为什么受害者还不走”,而是“为什么施暴者停不下来”,又或者“该怎么保护这个人”时,反家暴或许才会迎来新的转机。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结合这本书中的案例,来探讨家暴案件中受害者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与破局可能。
《看不见的伤痕》,[美]蕾切尔·路易斯·斯奈德著,蒋屿歌译,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当一头熊渐渐逼近,
你不会指望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米歇尔和洛奇是在周中放学后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在1993年,据她的朋友回忆,那次聚会上,不到14岁的米歇尔几乎是一下子就被比她大十岁的洛奇吸引住了。洛奇说起话来风趣幽默,举止谦逊,更重要的是,来自年长男性的示好带着自由的许诺,让彼时的米歇尔燃起了逃离父母羽翼的念头。即便得知对方曾因毒品交易蹲过一年监狱,这些也不足以吓退这个年轻女孩。两人很快确立了关系。
不久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一家三口从米歇尔的父母家中搬出来,尝试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庭”。没过一年,米歇尔又怀上了一个男婴,不到18岁的年纪却要照顾两个小孩,但米歇尔成熟得比所有人预想中都快。起初这个四口之家的经济很拮据,挤在一辆狭小的房车里,洛奇断断续续做过很多份工作,大多都耗费体力但赚得不多。不过,至少那时洛奇是“爱”着这个家的,他会在闲暇时教孩子们支帐篷、钓鱼,也像许多父亲一样把孩子举得高高的,在半空中飞。米歇尔呢?也是爱洛奇的吧,只是这种爱慢慢在似是而非的平衡中变得难以为继,她常常需要耗费巨大的能量来填补洛奇日渐膨胀的掌控欲。
美剧《大小谎言》(第一季)剧照。
洛奇的掌控是从小事中累积的。从一开始不让米歇尔化妆,到后来因为米歇尔想找份工作而发怒,洛奇一步步缩小包围圈,直到限制她邀请朋友来家中做客,试图切断她与外界连接的各种通路。而这一切,洛奇甚至不需要动米歇尔一根手指就能做到。他会在情绪失控时将孩子们带走,一连消失好几个小时,忧心忡忡的米歇尔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恐慌中等待孩子们安然无恙地回来。
有一次,两个孩子的外祖母来家中过夜。自从搬出来后,米歇尔与父母相见的次数屈指可数,可那天夜里,米歇尔说:“妈妈,你需要有自己的生活,不要总是过来。”这话的确出自米歇尔之口,可母亲总觉得,又不像是女儿会说出的。
转机出现在2000年前后。那年秋天,米歇尔怀疑丈夫有婚外情,尽管对方矢口否认,并在争执中打翻了米歇尔的抗抑郁药。这一次,米歇尔受够了,她将两个孩子带到父母住处,决心独自返回家中与丈夫对质。临走前,米歇尔郑重告诉母亲:“无论如何,不要让洛奇带走孩子。”
电影《亲爱的爱丽丝》剧照。
仅仅一个半小时后,愤怒的洛奇开车冲到了岳母家门口。先是用身体重重地撞着前门,后来又打碎后窗玻璃,穿过厨房到了客厅,用滴着血的胳膊猛地推开岳母,抓起沙发上的女儿冲回车里,离开了。回忆起那天,米歇尔的母亲依然无法忘记两个小外孙的神情,没有恐慌,没有尖叫哭泣,眼神呆呆的。“他们肯定见过这一幕。”
警察赶到时,态度冷淡,环顾一圈后询问米歇尔一家,想要以什么罪名指控洛奇。米歇尔的母亲疑惑,这难道不是警方该考虑的吗?最后,警方以强闯民宅为由处罚了洛奇,但报告单上既没有拍下碎了一地的玻璃,也没有提及滴着血的胳膊,更别说孩子们空洞的眼神,而只是写着当事人“在到岳母家接九岁的女儿(实际上只有7岁)时打破了后门窗户”。
也是那晚,米歇尔婚后第一次回到父母家中居住。她告诉母亲,洛奇曾经不知从哪儿抓回来一条蛇养在客厅,还说会趁米歇尔睡觉时放在她床上,又或是趁她洗澡时放进浴室,伪造出一场意外。漆黑的夜里,米歇尔语气飘忽,身旁是震惊到说不出话的母亲。
电影《隐形人》剧照。
母亲央求女儿把这一切写下来,去警局申请限制令,米歇尔也的确照做了。洛奇很快被关进当地监狱。那晚,朋友们带米歇尔去酒吧庆祝二十三岁的生日,这是米歇尔第一次摆脱洛奇的控制单独去酒吧,但那晚她只喝了一杯就起身想回家,说要和孩子待在一起。“洛奇试图让她相信外面的世界意味着危险,但不想让她知道,其实真正的危险来自他。”
然而,两天后米歇尔接到电话,“洛奇已被保释”。据说洛奇在狱中声泪俱下,哭诉自己什么都没做错,只是一个想接孩子的爸爸。电话这头的米歇尔神色大变,她母亲回忆女儿“吓得魂不附体”,对着电话大喊大叫,随后冲进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撤回了所有指控,“他从来没有威胁过我。没有蛇。都怪我。他是个特别棒的丈夫和父亲”。
那一刻,她对限制令的信赖崩塌了。蕾切尔·斯奈德在书中称,那几乎是米歇尔的本能反应。“当一头熊渐渐逼近时,你会猛地起身尖叫、虚张声势,还是躺下来装死?但可以肯定的是,当那头熊马上就要到你面前时,你不会指望得到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帮助。”
美剧《闪亮女孩》剧照。
被捆缚的受害者:
“为什么还不离开?”
米歇尔最终否认了指控书上所有的话,选择在所有人面前和洛奇站在一起,以表“忠诚”。这一行为或许间接导致整个事件的走势无可挽回。事发后多年,当时的检察官回忆起调查经过时称无能为力,“司法系统并不是为不合作的证人设立的”。可蕾切尔在走访中也得知,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每天都有凶杀案发生在不合作的受害者身上。为什么米歇尔她们选择留下来?
综合近年来多起发生在各地的亲密伴侣凶杀案,蕾切尔发现这些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她们曾一次又一次尝试过任何可能的办法,却无一例外都在诸多外部力量撤出后,刺激那头正在逼近的熊变本加厉。从身边的亲友到警方,他们的表现都像是在告诉当事人:“你太夸张了”“事情没那么严重”“他只是想见见孩子”…… 这些判断渗透着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男人是强壮的,女人是柔弱的,男人是理性的,而女人是歇斯底里的。洛奇被保释的那一刻所传递给米歇尔的信息是,“体系也将我的自由置于你的安全之上”。
延伸阅读《他为什么打我:家庭暴力的识别与自救》,[美]伦迪·班克罗夫特著,余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11月。
即便米歇尔带着孩子逃出去,她们又该如何生活?米歇尔没有收入和工作经验,那天洛奇强闯娘家已经表明这些都无济于事。当人们一遍遍追问“为什么受害者还不跑”时,体系中的漏洞早就筛过了“该怎么保护这个人”这类再实际不过的问题。对于米歇尔而言:“世界之大,那个男人会倾尽所有找到我。”
换言之,米歇尔选择的不是“留下来”,而是“活下去”,蹑手蹑脚地走向属于她和孩子们的自由。慢慢地,受害者学会了一套安抚愤怒配偶的方法——恳求、哄骗、发誓,以及在公开场合与配偶立场一致,以此为自己争取安全脱身的时间。她们甚至可能无法意识到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直到凶杀案发生的前一刻,都怀抱一线希望,觉得只要孩子在身边,对方就不会伤害自己。
落到具体的家庭关系中,形势的变化常常难以捕捉。操纵大多很隐蔽地潜伏着,而且往往是由那些低级的攻击和威胁所构筑的。在《胁迫掌控:在生活中男人如何使女人陷入罗网》中,埃文·史塔克称百分之二十存在家暴的关系中没有出现肢体暴力,他将这种在不伤及受害者肢体的情况下,主导其日常生活的方式称为“胁迫掌控”。而在胁迫掌控中,外人看来的威胁可能会被当事人解读为爱,特别是在其中一方极其敏感脆弱的情况下。对于米歇尔而言,真正的捆缚在于即便她感知到自己在家中是个“被强迫的人质”,她也很难相信,一个爱着或曾经爱过的人真的会危及她的性命。
美剧《大小谎言》(第一季)剧照。
更艰难的是,大多数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时刻是波峰式的。当愤怒的施暴方事后道歉时,讲述着自己也曾是某段关系中的受害者,以及自己又是如何在同原生环境遗留的阴影艰难搏斗,这时,选择再一次原谅的米歇尔们并不仅仅是幻想对方会真的改变,而是那一刻她们同样产生了向内的自我怀疑,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包容”“是不是我的方式不对”。亲密关系的复杂性也恰在于此,双方都完全地看到了对方的“强大”与“软弱”,“暴虐”与“依赖”,而同这种“软弱与依赖”作斗争才是最难的。
失控的障眼法:
“为什么施暴者停不下来?”
米歇尔一家最后死于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洛奇在开枪击杀妻子后,杀死了家中的两个孩子,随后泼洒汽油点燃了房屋,最终回到地下室自杀。警方赶来时,房子里浓烟缭绕,一切看似无法用逻辑去理解。那一晚,洛奇“失控”了吗?这个词在家暴或亲密伴侣凶杀案新闻中反复出现,可实际上,失控的瞬间并不存在,暴力是一种选择。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研究都曾将家暴归因于“疯女人”激怒了她的丈夫。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国反家暴倡导者埃朗·彭斯提出“权力控制轮”(Power and Control Wheel),归纳在实际关系中,施暴者持有权力与掌控对方的方式大致有八种——恐惧、情绪虐待、孤立、否认和责备、利用孩子、欺凌、经济控制,以及蛮力和言语威胁。研究还表明施暴者大多会否认自己真的在实施暴力,倾向于用“没那么糟糕”来弱化暴力的程度,并指责受害者反应过激,他们不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寻求权力与掌控。一旦感到“世界亏欠了自己”,需求没有被满足,信仰系统面临挑战,这些就被自动归结为“真男人”遭遇的致命危险。于是“真我”消失,“内心的杀手”开始行动,而杀手不会有愧疚感,因为杀手不是“我”。
《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英]简·蒙克顿·史密斯著,尹晓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9月。
此外,语言往往在家暴中被挪用,成为暴力的组成。为了巩固暴力的合法性,施暴者会用不同称呼指称对方,那一刻房间里没有“米歇尔”或是“阿莉莎”,有的只是“荡妇”和“疯女人”。在这些新名字下,暴行本身在施暴者意识中就成了站在情理一方的合理惩戒。而在事发后,施暴者往往会表示懊悔并流泪致歉,“如果不是因为我如此在意你,我就不会这么生气”,将此前施加的暴力与内心的嫉妒浪漫化,并完成了对杀手行为的自我开脱。
更遗憾的是,施暴者看似都是暴怒的人,然而事实上,这种暴力是有特定指向性的,以至于我们无法轻易将他们从人群中辨认出来。走访中,创建了美国第一个施暴者干预项目的亚当斯称,极度自恋是解读施暴者的关键,而这类人往往看起来十分正常,且有着出众的人际交往能力。更何况家暴对施暴者的影响要小得多,施暴方既不会因此失眠,也不会失业,“他们很有魅力,而受害者的表现则很负面”。因而,施暴者也常将自己视为某种程度上的拯救者,渴望被人感激。
美剧《大小谎言》(第一季)剧照。
尽管实际案件中,也存在部分女性实施暴力,但蕾切尔在书中并未避讳称,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所有公开的家暴与其他形式暴力的数据表明,绝大多数施暴者是男性。然而,暴力中的性别问题经常是公共领域中那个“房间里的大象”,而拒绝正视“谁在施暴”的分析方式一直阻碍着我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案。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根源于男性普遍认同的信仰体系,在这套观念下,男人成为男人的方式是证明自己比其他男人和女人优越,而强迫与暴力正是在觉察到自身的权威受到挑战后,继续维持习得的自身优越感的方式。
悖论在于,在这套体系中被拱上等级顶端的男性也从来不是体系本身的受益者。研究暴力的学者詹姆斯·吉利根发现,对于许多男性而言,使他们震惊的是意识到自己也被更强大的力量操控着。换言之,如何成为一个男人的观念本身是被灌输的。他们被告知,作为一个男人,可以表达愤怒、展示权威,但不能有同情心、善意、恐惧、疼痛与悲伤这些被认定属于女性的气质。他们可以通过暴力消除内心的痛苦,但不可以流泪。归根结底,这是一种既压制受害者,也压制施暴者的文化。
与此同时,当意识到自己是被塑造成施暴者,而不是天生喜欢施暴,这一点也使施暴者如释重负,且往往这一刻,才是他们真正产生改变的开始。
美剧《大小谎言》(第一季)剧照。
尾声:
在暴力升级前制止暴力
回顾整个案件,社会干预的缺失在其中起了加速性的作用。蕾切尔·斯奈德认为,以警方为代表的外部力量之所以对事件本身轻描淡写,除去“家暴”定义中“家”概念对暴力本质的弱化与模糊外,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的社会也缺乏适当的培训机制,无法在暴力尚未升级时提前加以制止,或者说缺少更为有效的“风险评估工具”。
这就涉及我们如何界定暴力的升级。根据数据统计,扼颈通常是亲密关系凶杀案发生前的最后一项虐待行为,可在实际诊断中却很难发现。受害者经常无法记起自己被施暴的全过程,复述具体情景时也用词模糊,不断改口变更具体细节,甚至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当时已经失去意识,这些在外界看来很像在“撒谎”,但其实是脑损伤的症状之一。而当医疗机构或警方仅仅凭借是否有明显可见的伤痕作为判定依据时,许多受害者的创伤就被低估了。诸如失忆、声音嘶哑、小便失禁等不明显症状应该更多被纳入对受害者的问询和检查流程中。
电影《隐形人》剧照。
一旦暴力被识别,如何保护受害者就成了更为切实的问题。在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设立的庇护所曾是为解决家暴问题的第一次全国性尝试。它既可以是旅馆里一张过夜的床,也可以是居民区中由多个家庭公用公共空间的独栋住宅,为的是给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和孩子提供一个摆脱过去生活的可能。但是数十年的实践中,这种“庇护所”常常会变质,提出庇护申请的受害者大多被视作“救济金的领取者”,由于资源分配受限,获得庇护的代价可能是辞职、远离家人朋友,以及孩子离开熟悉的学校等。这些场所甚至会明显标识隶属反家暴机构,身份的标识可能招致心知肚明的异样眼神。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是更加关注受害者自主权的“过渡所”。
除此之外,家暴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打破暴力的循环。据蕾切尔·斯奈德调查,美国民间多地正在尝试组织专门面向家暴家庭孩子的“希望夏令营”,甚至还有针对暴力中施暴方开设的求助热线,为那些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但不具备情绪控制能力的施暴者提供心理援助。这些具体举措都需要配合系统性的变革和整体社会意识的更新。斯奈德在后记中提到,电影《暮光之城》中男人会在女人睡觉时盯着她,而当我们的大众媒体仍然在把这类跟踪行为无限浪漫化时,年轻一代又如何能意识到亲密关系中病态控制的威力?
作者/申璐
编辑/青青子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