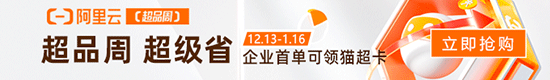英国国家元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殷之光】
2019年夏天,在美国驻英大使官邸举行了一场小型宴会。时任美国驻英大使、商人罗伯特·“伍德”·约翰逊针对英国退欧做了一段简短的即兴发言。
发言中,伍德先是对英国“莫名其妙地就切断了跟自己最大贸易伙伴的一切联系”表示不解,“什么样的国家会干这种事情?”伍德不客气地问道。在场的英国宾客们都感到了些许的不适,毕竟在外交场合,一名大使这么不客气地抨击驻任国,实属不寻常。
伍德问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停顿了一下,吊足了在场听众的胃口。“我们会这么干!我们这么干过!美国就会这么干!你们做了一件非常美国的事情。你们把信仰托付给了自决(self-determination)与自由(liberty)。”
特朗普时期出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四世(图右)/资料图来自AP
相比他的美国驻英大使头衔,罗伯特·“伍德”·约翰逊的另一个身份可能更广为人知,他全名是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四世,是美国医药与医疗器械巨头强生集团创始人罗伯特·伍德·约翰逊一世的曾孙、强生家族巨大财富的第四代继承人。正如他的曾祖父一样,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四世对英美联盟(Anglo-American Union),塑造一个全球性的霸权秩序表示出了极大热情。只是相比19世纪中后期那种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今天的人更乐意用“英美特殊关系”来表达这种特殊的纽带。对其信仰者而言,这种两国联手治理天下的美梦,是实现“自由”与“繁荣”的唯一“文明”途径。
出席了2019年那场宴会的人里,有一位出生于英国西南小镇托基(Torquay)的保守党女议员佩妮·莫当特(Penny Mordaunt)。她后来出版了一本题为《更加伟大:风暴之后的不列颠》的小书。在开头的序言中,她生动地描述了这次聚会的场景,并评论道:“相较于我们各自的邻国而言,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共同点要多的多。……尽管我们中间隔着一个大洋,我们的秉性是相通的。”
英国首相约翰逊辞职后,佩妮·莫当特这个名字变得更加出名。作为保守党接替首相职位的候选人之一,她是诸多候选人中最受保守党普通党员欢迎的一位。不过,在刚刚结束的第五轮投票中,莫当特不敌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在前四轮均领先的情况下,第五轮被特拉斯反超,获得105票位居第三,无缘终决选。
今天的观察家们,通常会用“英美特殊关系”来描述这种纽带感情。实际上,早在1946年3月开启全球冷战对抗的“铁幕”演讲中,丘吉尔便用了“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这个字眼。他强调,“说英语的人民之间那种兄弟般的联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丘吉尔所说的这种充满殖民帝国种族主义味道的“兄弟”情谊,当时并未引起太多美国方面的共鸣。
约翰逊收到的临别礼物是议员们凑钱买的丘吉尔回忆录
毕竟,在二战之后全球巨大变局的背景下,美国人相信,未来的时代将会是一个“美国世纪”。在这个“美国世纪”里,与英国分享霸权,并承担英帝国全球殖民帝国分崩离析的历史负担,这绝不是一个合算买卖。战后的美国,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物质基础上,似乎都为制霸全球做好了准备。在丘吉尔冷战演讲时,美国塑造战后全球秩序的工具箱里,就已经有了一件核心武器,即通过1944年《布莱顿森林协定》确立的美元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有了世界银行、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新成立的联合国也基本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和掌握之下。同时,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GATT)等在军事、内政、经贸等方面深度绑定亚欧与美国关系,确立美国在欧亚霸权的工具也基本成型。
如果说,1941年签署《大西洋宪章》时,美国希望向全球推广罗斯福“新政”(New Deal)秩序的野心还仅仅停留在“理想”阶段的话,那么随着日本与德国的战败,欧洲其他19世纪霸权国家的衰败,美国秩序走向全球,在此刻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距离它成为真正的现实还缺少一个更为原始的驱动力——一个强大的敌人。
霸权的世界秩序观依赖两个简单但却必要的结构力量:理想与敌人。这种二元论的秩序观通过对敌人的恐慌,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最大规模调动;通过对未来蓝图命定论式的描述,让人们相信自身所经历的困境与苦难,都仅仅是“暂时”的。这样,个体就不仅成为了具有执行能力、可被“操纵”的机器,也可以从这个过程中,获得“超越自我”的神圣体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为理想的工具。
随着二战结束,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很快便被诸如乔治·凯南等一些期待建设美国全球霸权秩序的战略家们树立为“自由和平”的敌人。而来自丘吉尔的铁幕演讲,进一步促成了华盛顿政府的态度。虽然,此时的华盛顿对丘吉尔所希望的英美“兄弟联合”兴趣不大,但铁幕演讲中所描绘的那种包含了西欧国家的“自由世界”联合,与亨利·鲁斯(Henry Luce)的“美国世纪”理想、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对“西方世界”团结的认识、以及雷克斯福德·特格威尔(Rexford Tugwell)将罗斯福“新政”推广至全球的追求,产生了极大共鸣。
虽然,二战之后的美国无意让英国通过“英美特殊关系”来搭自己全球霸权扩张的便车,为旧有的以英国为中心的“共荣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全球霸权续命。但是,无论是在亨利·鲁斯、克雷斯福德·特格威尔,还是乔治·凯南的全球秩序理想中,英美之间的团结都是这种秩序的核心基石。维系这一关系的,除了带有新教情怀的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精神之外,对许多政客而言,是否为这种“特殊关系”赋予实质性内容,则是霸权竞争、消长过程中,以利益为中心的选择结果。
在1940年法国投降前,当时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还就是否邀请美国参战一事犹豫不定。就在这一年初,他就向自己的妹妹艾达·张伯伦透露过对美国的不信任。他提到,自己“不想让美国人为我们战斗”,因为美国参战并取得胜利之后,英国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他的继任者丘吉尔,虽然在法国投降后非常积极地希望美国加入战争,但同样也不希望英帝国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与全球贸易的优势拱手让给美国。就在这种相互猜忌,但却难以分离的纠结关系下,英美主导签订了1941年《大西洋宪章》,勾勒了战后以两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格局。
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全球格局可以被“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这个没什么历史负担的字眼来概括。但对英国而言,“新”的国际秩序则像是20世纪初英国霸权主导下的“英联邦”的扩展版。因为这种“自由国际主义”提供的秩序理想,几乎复刻了“共荣联邦”用“自由”“自治”“平等”“自由贸易”“宪政”等宏大字眼勾勒出的图景。
从精神本质上来看,无论是19世纪的英帝国、还是20世纪初的“共荣联邦”亦或1940年代之后的“自由国际主义”,都是同一个资产阶级世界帝国的不同外衣。但是,在全球霸权的具体实践上,这种秩序理想依托的霸权中心随着二战的发展,从英国最终转移到了美国。并且,在此过程中,一个19世纪不惮于用“帝国”来作为骄傲自称的全球霸权秩序,随着二战后民族独立浪潮、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规模兴起,而不得不将自身隐藏在一套更加精细、更具“普遍性”的制度设计之中。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帝国”重新变为对敌人的蔑称,而“帝国主义”则悄然躲藏在了这套精细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设计背后。
在二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旧帝国霸权的衰落让不少人相信,帝国时代业已终结。然而,反观这段历史,越来越多人也开始发现,现实更像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帝国”中心在进行着转移,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自己隐藏在一系列干涉行动、代理人战争、经济援助、贸易协定背后。随着20世纪末,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旧殖民资本主义帝国形式上的彻底瓦解,完成了中心转移的霸权开始迅速露出了它的獠牙。对英国而言,盎格鲁-美利坚的“特殊关系”又站到了前台,作为精神桥梁,更是作为呼吸机,把垂死英国的生命搭在了美国霸权的机体之上。
1999年,就在科索沃危机的当口,当时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Economic Club of Chicago)上的讲话中,通过颂扬自由干涉主义、美国全球领导权,再次将“英美特殊关系”推到了历史前台,并将其描绘为全球谋求“民主与人权”斗争的锚点。
而对美国来说,二战之后那些遮遮掩掩用来掩盖美国全球霸权的国际制度设计,随着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敌人”的解体而变成了累赘。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们开始鼓吹一个以“全球化”为名的变革。改革联合国、谋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银行、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获取更大主导地位等等,都是这一“全球化”包含的诉求。
与此同时,美国的外交智囊们,也开始以“新现实主义”为名,强调一个霸权中心世界秩序的必然性。此时,美国出现的霸权中心秩序观,更乐意描绘权力间合作维持既有秩序的可能性;强调世界和平秩序必须由霸权或几个霸权、甚至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来达成。
一个霸权衰落而空出的位置,必然会由另一个霸权来替代。而霸权交替则必然会伴随着战争。虽然美国的新现实主义者们用“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这个术语替代了充满负面含义的“霸权”,但毫无疑问这种“和平”几乎就是19世纪欧洲“权力平衡”结构的翻版。和平可以暂时存在于几个强权国家之间,而在更大世界范围内,则全然延续着19世纪强权国家宰制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秩序。而且,在这种霸权平衡的和平秩序中,美国毫无疑问通过其强大军事实力、美元的霸权地位、以及对市场的操纵能力扮演着“体系中的霸权”角色。而“英美特殊关系”以及以此为中心向G7国家的扩展,则成了这种国际合作机制必不可少的装点。
2008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这种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秩序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同时,在自由干涉主义名义下,美国在南联盟、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等欧亚非大陆各个角落进行的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也逐渐将美国推上了一条英帝国霸权晚期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在二战后既有国际体系内的坚强崛起,也更让美国对自己一手构建、本以用来隐藏帝国的全球机制产生了强烈不满。因此,中国也成为霸权者维护全球野心过程中,寻找到的一个新的、但却截然不同的敌人。
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便通过退群、破坏国际规则等手段,开始试图重新架设一个稳定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作为盎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搭便车”者,英国也在这一“英美特殊关系”的奇怪关系中越走越远。2016年的退欧,虽然显得有些出人意料,但也不失为这种捆绑关系的合理结果。
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双方进入11个月的过渡期;并于该年底,英欧领导人签署脱欧贸易协议。资料图来自AP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欧洲重新回到了战争恐慌之下。战争就像是欧洲的痼疾,在资本主义全球霸权野心的驱逐下,每隔数十年,便重回大地。英国面对战争的积极拱火态度,也更充分地展现出对这个已经衰落的霸权中心国家而言,“英美特殊关系”是它续命的神药。经由“英美特殊关系”这一种族中心的桥梁,在大西洋彼岸的亚欧大陆的最西端,放下一个“同种同源”、包含“兄弟”情谊的同盟,也是美国为自身霸权续命,维持对欧亚战略影响的必要手段。这种由霸权本身发展而决定的关系,会因历史局势的变迁而在台前幕后不断出入,但却永远不会消失。
与之相比,2022年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辞职,仅仅是一场保守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之后无论是哪位候选人接替首相职位,都不会对既有的局面形成任何有意义的影响。更不会对中英关系的现有形势,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霸权的特点在于它永远需要一个敌人。在与敌人的竞争过程中,霸权完成其自身理论普遍性的自我确证。正如邓小平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说到的,霸权关系“不是你压到我,就是我压倒你”。而恰是这种霸权竞争,为霸权本身“设置了对立面”。在这份讲稿的官方英文译稿中,“对立面”被恰如其分地翻译为“antithesis”。的确,霸权本身包含了自身的反题。而这个反题,就是“各国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这个解放,不仅包含了形式上的政治独立,更重要的是在平等互助与独立自主原则下,完成经济、文化、社会的彻底解放,从帝国主义的霸权秩序中脱离出来,走出一条属于亚非拉、属于被压迫者真正的自主、互助、平等道路。
霸权的反题是解放,这反应了毛泽东于1970年代形成的“第三世界”认识。在1970年6月19日接见索马里代表团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并提出,“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他们去搞他们的大三角、大四角、大两角好了。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可以看到,无论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平衡的秩序观,本质上都是“想控制人家的国家”,在强权宰制之下“讲平等、讲自由”。而就不同意图谋求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讲平等,就不肯让你们自由、让我们自由”。毛泽东这种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走大国沙文主义道路的秩序观,到了1974年2月会见卡翁达时,更具体地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三个世界”表述。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接见卡翁达。
1970年代的中、美、苏“大三角”叙事,与今天美国学界与媒体不断尝试强加于我们的“中美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等叙事异曲同工,无外乎是霸权中心主义对反霸权实践的话语规训。而从第三世界出发,平等的内涵则更为丰富。它与合作相互并存,包含了谋求发展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任务,也传递了经济与文化独立的诉求,同时还强调了谋求国际之间实质民主秩序的重要意义。
这一系列在第三世界、在全体被霸权压迫的国家与人民自主反抗进程中展现的诉求与认识,可以用“解放”来概括。这便是对第三世界主权平等观的准确说明。用万隆会议的表述就是,人民的解放就是经济、文化与政治的系统性“去殖民”。霸权力量与霸权格局的消亡,才是人真正自由的到来,也是这种解放的最终理想。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