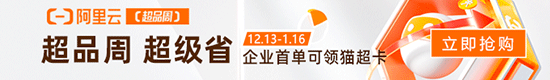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风格 后现代风格的代表人物
在谈论艺术时,人们经常使用“古典”“现代”和“后现代”来给某一种艺术或某一件艺术作品定性。这三个词在我们的日常话语中并不陌生,不过,当它们被用于艺术的语境之下时,你真的了解它们的含义吗?
古 典
古典艺术往往与真实相联系。在古典的艺术话语体系中,如何借助线条、形状、光影、色彩等手段,创造出如其所见、所知、所感的视觉真实,是艺术家的首要任务。
所谓视觉真实是指在接受者的观看模式中,造型艺术的符号与它所再现的世界之间具接受效果上的“似真性”。之所以说“似真”是因为艺术符号再现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表象的世界。
艺术与世界的关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既在形态上有几分神似,又不完全一致;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妙在不即不离,既贴近生活,又融合了艺术家创造性的想象。这种熟悉的陌生感或陌生的熟悉感,让接受者感到艺术的世界生动如真。虽是幻象,但具有接受效果上的真实感。
说它是幻象,一是因为艺术的再现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需要对现实世界进行复杂的中介处理,艺术的效果取决于再现的媒介、对象与技艺;二是因为艺术的再现是一种“观物取象”的抽象过程,再现什么、如何再现取决于艺术家观察自然的眼光或图式,“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
说它是真实,一是因为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指涉物之间具有约定俗成的指涉关系,它以外在的自然、人生为参照,让接受者通过造型符号看到了符号指涉的世界;二是因为“诗比历史更真实”,它并不叙述时空中偶然的事态或个别的事实,而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描写历史发展中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的事,表现人生普遍的情绪与意义。
简言之,它不仅呈现了表象的世界与人生的幻想,而且揭示了隐含在表象世界之中的历史真实与心理真实。因此,作为幻想的制造者,艺术家不仅呈现表象的世界,而且建构视觉的真实。
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古典大师,用完美的技艺不仅把自然的微妙描绘得淋漓尽致——有完善的规则、严谨的次序、准确的比例、精湛的素描和神奇的优雅,而且赋予他所创造的形象以情感和生命。
在古典的艺术世界,艺术家总是在所知(Knowing)与所见(Seeing)之间做出妥协和选择,从而使古典艺术处于相对和谐的境界。有时候艺术家重视自己的视觉认知,需要把所有要素尽可能清楚地呈现出来;有时候艺术家希望忠实把握特殊时刻、特殊视角下的完美瞬间,如其所见地呈现自我感知的世界。
现 代
与古典的和谐不同,现代话语具有鲜明的断裂与危机感。那种连续、一贯的生活感受和不断渐进的艺术史观消失了,现代艺术家感到一种吓人的裂缝横在传统的过去和遭受震荡的现在之间。没有传统的延续和确定的规范,现代艺术转而强调“绝对的现代”,强调流动、变化和偶然,以及对艺术陈规的质疑。
现代艺术家抛弃了对外部自然和现实世界的真诚,转而痴迷于视觉印象的真实和转瞬即逝的美。尤其从塞尚、高更、凡·高以来,在对视觉现象的重估中,他们抛弃了三维空间的幻觉,“越来越大胆地切断艺术中的再现因素,以便越来越坚定地在至为简洁、至为抽象的要素中,确立其表现形式的根本法则”。
现代文化以自我塑造为核心,它鼓励独立自主和表现的自由,给予自我探索尤其是感情方面的自我探索以重要地位。一方面,这种自我表现与探索侧重于个人的经验与趣味,对艺术价值的评价不再依据艺术界的共识,而是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另一方面,它又是反体制的、批判的,尤其是对资产阶级酷爱秩序心理的激烈反叛。
它以放荡不羁的形式表达了拒绝媚俗的精英意识,无形中拉大了精英与大众的距离,使公众在鉴赏活动中对现代艺术日益冷漠疏远。用西班牙美学家奥尔特加的话说,现代艺术与大众格格不入,注定无法通俗,它根据受众的反应把芸芸众生分成了两类彼此对立的人群:少数理解艺术的人和多数因不理解而痛恨艺术的人。
艺术家与公众的疏远是艺术意义危机的一种症候。它使现代艺术陷入深刻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形式的锐意革新和鲜活的审美经验强化了艺术的间离效果和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形式的激进创新和意义的晦涩难解又使现代艺术日益自恋,成为象牙塔式的小圈子艺术,失去了“介入”生活的社会效用。
后现代
如果说现代艺术以艺术的自主性为前提,刻意拉大艺术与世界、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精英与大众、雅与俗的距离,那么后现代艺术则产生了“距离的消蚀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
在艺术体制上,后现代是对占领着画廊、博物馆、美术馆、基金会等机构运作的盛期现代主义的刻意反动,对精英的、纯粹的、自律的、小圈子的自主性艺术机制的反动。在艺术风格上,雅俗艺术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已经失去了泾渭分明的界限,人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号拼贴的混杂风格之中,现代美学一本正经的精英意识已经被戏谑的、嘲讽的审美立场取代。
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我们见证了艺术与世界从“不即不离”到拉开“距离”,再到“距离的消蚀”的过程。
由于货币和信贷的作用,以及技术的宰制,现代社会越来越有抽象化的组织功能和算计功能。这种算计功能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算术题,人的价值也随之变成市场上可计算的符号价值。在公共领域,主体间的交往是以功能理性为主导的,这无疑拉大了主体间心灵交往与沟通的距离。
与此同时,借助现代化的信息媒介和交流工具,那些远方的东西和异乡的人们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显然,这种空间距离的克服,是以心灵距离的疏远为代价的。在大都市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漠和麻木,人们对自己近距离接触的人与物越来越感到震惊。
当然,在物化的现实面前,拉大的不仅有心灵的距离,还有社会的距离。在消费社会,文化资源占有的多少,日益成为现代人获得身份、地位与财富的标志。那些精英阶层由于接近文化资源的中心,在社会的变动中更容易扩大象征资本的积累。
与之相反,弱势群体越来越远离文化资源,也就越来越贫困和“低贱”。对后者而言,人们日益感到客观精神文化对主观精神文化的挤压,感到“人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此意义上,现代艺术借助审美的距离来克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的方法,无疑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和补救功能。
在后现代艺术中,伴随着雅俗文化的融合以及不同风格艺术的混杂,这种距离感消失了。人们片面地强调直接性、轰动性、震惊、新奇和刺激,消解了时空感受的审美距离。
后现代艺术的主要策略是,通过对过去符号的拼贴、挪用、解构与重组,来消解文化与经济、信息与娱乐、现实与影像、精英与大众、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差异性。因此,后现代艺术往往不像现代艺术那样给人很强的距离感,与此同时,它的批判性也相对减弱了。
- 版权信息 -
编辑:子水 黄泓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
图片来自网络
《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
作 者:周计武 著
探讨艺术思潮,辨析现代艺术观念,重构具有中国人文底蕴的艺术理论体系。
点击阅读原文一键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