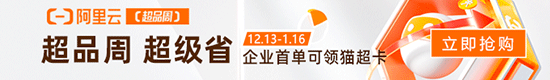王小波黄金时代 王小波死因
“你好哇,李银河。”就这一句话,不知多少人爱上了王小波。
现如今,人人都想找个“灵魂伴侣”,许多人都是受了王小波的影响。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正是王小波本人的写照。
当时李银河虽倾慕王小波的才华,但还是觉得他太丑而与他分手,王小波痛苦不已,在信中写道:“你从这信纸上一定能闻得见二锅头、五粮液、竹叶青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
别说李银河了,任谁读到这样的信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王小波确实有趣,并且不是那种耍滑头式的抖机灵,而是真诚、幽默,又带着对人的珍视和尊重,所以李银河最终被他的才华折服,读者也因为他的作品而将他视为精神偶像。
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列为禁书,在香港出版的时候也被迫改为《王二风流事》,俨然艳情小说。直到后来才解除封禁,而王小波,也是在死后才因作品被中国观众所熟知,甚至被奉为青年领袖,引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
等解了禁,王小波就火了,火了一波又一波,直到我刚考上大学那会儿,还总是听说王小波的作品。大概我们再难找到一个哪一个作家像王小波那样,语言诙谐有趣,格局却宏大如历史,看似蜻蜓点水,实则在未说之间把一切都说了的作家吧。
一、看《黄金时代》的三重境界
人们常常用这几句话来形容人生的境界:“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这话对好作品同样适用。
有的人把《黄金时代》当性启蒙来看,有的人从其中寻找爱情,而有的人读出人生的方向。
许多人说不清爱情是什么,但当很多人嘴上说着爱,其实要的只是性,那时正是文革年间,陈清扬和王二被拉上台批斗,交代一次又一次,上面人不断等着看交代材料,找的也不过是性,所以当看到陈清扬坦坦荡荡将自己爱上王二的那一瞬间记录下来,却让那群领导们一个个看得面红耳赤,停止了无休止的盘问,再也不让陈清扬和王二去写材料了。
这一点,甚至王二也没明白。最初似乎是王二拯救了陈清扬,将她从孤立无援中拉出来。后来却是两人相互成就,甚至当陈清扬彻底理解了“命运就是遭受摧残”这一本质后,她一下子清醒了,比王二更早地接受现实,甚至学着与现实和谐共处。
二、陈清扬:永远的经典
读完《黄金时代》,再也忘不掉陈清扬的名字。国内再没有哪个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如此迷人,她从迷蒙到清醒的过程,仿佛带着启蒙的意味,这不只是对女性而言,而是对整个人类而言。
从被叫“破鞋”开始,陈清扬就活在人们这恶意叠加的枷锁里,于是好不容易遇上个真是来找她看病——而不是借着“看病”来骚扰她的王二,陈清扬就忍不住追上去,想让他证明她不是破鞋。
但这整个大时代的混乱与扭曲哪是一两个人能扭转的,王二当然证明不了陈清扬的清白。
彼时还有点中二气的王二倒是对人生的各种混乱已经有些体会,他很清楚人们的想法是难以改变的,也劝陈清扬早早放弃所谓的“清白”:因为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从污蔑别人中取乐,这就够了,没人关心事实是什么,也不管被造谣者会因此遭受什么打击。
所以陈清扬从燃起希望到希望破灭,这中间并没有经历太多时间。
但她还是被王二口中的“伟大友谊”迷惑住了,于是为了讲义气,和王二墩伟大友谊,为了抵御被说“破鞋”的攻击而成了真正的“破鞋”,一方面是对命运的屈服,倒又像是对命运的讥讽。
但不管怎样,当她真的不在乎别人的污蔑后,哪怕真做了破鞋,人们的态度却全然不像先前那样可怕和令人窒息了。就像王二所说的那样:“那里的人习惯把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正的破鞋放任自流。”
陈清扬原本是个对一切都颇有些淡漠的女子。遇到王二之前,她是迷蒙的,茫然的,迷糊又清醒,想反抗又无从下手,她不理解: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件事为什么是这样的?人们为什么这样?她怎么会活在别人嘴里?
但她早已经对命运的恶意有所察觉:
“陈清扬说,在此之前二十多年前一个冬日,她走到院子里去。那时节她穿着棉衣,艰难地爬过院门的门槛。忽然一粒砂粒钻进了她的眼睛。这是那么的疼,冷风又是那样的割脸,眼泪不停地流。她觉得难以忍受,立刻大哭起来,企图在一张小床上哭醒,这是与生俱来的积习,根深蒂固。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奢望。”
后来,她凑合着嫁了人,又回归到孤身一人,明明清白无比,却被人人都叫成破鞋,她想要脱身,但总是被无形的手捆绑着。
那时候,她就渐渐明白,这世界好像是不讲道理的,人总是在受苦。她不再哭了,因为没人会怜悯一个流泪的人,在这个人人受苦的时候,眼泪是不值钱的。
直到遇见王二,在他半忽悠半真实的教唆中,她突然觉得一切还是有转机的,起码面前的这个人,和她一样有着对生活的热爱。
所以哪怕她早已察觉王二此刻只是在忽悠她,但她毕竟从没听过“伟大友谊”这个说法,她感到窥探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活法,好像有着什么东西能带她破除眼前的迷障,跳出这闷人的世界去。
后来,她的确在王二身上发现许多特质,他一点也不圆滑,好像什么都要冲破头脑。但他又尽情地活着,哪怕腰痛得弯不起来,哪怕身无分文,却比她以往见过的所有人都要活得精彩。
在王二的引领下,陈清扬完成了蜕变。那时,陈清扬26岁,王二21岁。
陈清扬比王二更早地感受到命运的摧残,也更早地“接受”命运。但她的这种接受并非如文革时期的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自私自利地去害别人,她只是看清了生活的本质就是受苦,所以便“高兴地接受摧残”,允许一切的发生,懵懂又默然,但又没有失去生命的热情。
“我只愿蓬勃生活在此时此刻,无所谓去哪,无所谓见谁。那些我将要去的地方,都是我从未谋面的故乡。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
陈清扬领悟了,所以她日渐坦荡。甚至还学会了与生活共舞。后来批斗的时候同是被捆绑,王二的手经常被捆得乌青。而陈清扬却经常说话,“她说:大嫂,捆疼了,或者:大嫂,给我拿手绢垫一垫。我头发上系了一块手绢。”处处与人合作,连挨批斗似乎也像家常便饭一样了,这样的境界,我还真没在当代别的女性角色身上看见过。
《黄金时代》的一个神奇点是,虽然不避讳性描写,写的也是王二的男性视角,却比许多知名作品都显得要尊重女性。
因为这里面没有强化性别对立,也全然没有男女任何一方的优越论,全都是出自本真的思考,既自然展现了男女各自的特色,也显示了男女的合作,甚至都没有那么突出性别,就仅仅是两个朋友的交往一样。与那些性别建构明显的作品全然不同。
王二作为第一视角的人物,也是王小波的化身,自有他的可爱之处。而王二描述中的陈清扬,也完全没有片面化和单一化,性格丰满,角色立体,有着无限可爱,甚至比王二获得了更多的读者青睐。这是非常进步的一点。
以前很喜欢严歌苓,她写的女性写得好,色彩浓烈,情绪也细腻敏感,只读文字就像看了场电影。但角色同质化比较严重。而且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的女主人公却总是依附于男人存在,永远是爱情至上的模样,好多时候失去自我,处于一种奉献的母性状态,王葡萄、小渔、穗子、田苏菲……虽年龄不同阶级不同环境不同,但都是永远追逐爱情、为爱奉献、甚至因爱痴痴或者地母的典型。
而许多其他广受好评的男性作家里,被叫好的往往是作品整体思想和男性角色的塑造,对于女性的描写要么是薄弱,动不动就到“少女和妖妇”的传统老路上去了,让人看了乏味。
直到看到陈清扬,我才终于找到一个独立、坚强,清醒又不失浪漫意气的女性。她被王二唤醒,又带着王二往前走。她比王二更清醒,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这个世界,了解面前的王二。但她也接纳爱情,任爱情来去,珍惜身边的一切。同时又允许王二的不爱,或者是逃避。
所以她会说“好危险,差一点爱上你”,也会一时动情时说出给王二生一窝崽子这样的话,但在王二岔开话题后断绝了念想,直到分开许久,各自婚嫁,才在重逢后把爱上王二这件事告诉他,然后坐上火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三、永远的“黄金时代”
王小波的文字是坦荡的,塑造的角色也是坦荡的。综合他的所有作品来看,小说里写得能称之为“圆融”的,唯有《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就像河流,有时像涓涓流水,有时如奔涌江河,恰巧像不断流转的岁月,如同宇宙间的斗转星移。
这字里行间有一种坦荡的纯洁,一方面来自于王陈二人直爽真诚的性格,另一方面来自于王二对意气和信仰的执着:“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 ”
干净的景物描写让这执着更生动,也更明亮。无论人世间怎样风云变幻,云南怎样闭塞落后,天上的云、太阳、星星……总是不变的美丽。
陈清扬和王二在追求上是一致的,但生命本质上确实不同的,就像男女天生有别一样。王二总是邋里邋遢,哪怕最后文革结束回到内地,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土流氓。而陈清扬当了副院长,全身上下都是个“香喷喷的LADY”。批斗的时候王二从不讲话,而陈清扬则处处与人合作。
陈清扬从开始就是极美的,和王二看起来格格不入。那会儿两人避山隐居:“每到跨沟越坎之处,她就找个树墩子,姿仪万方地站上去,让我扛她。”这个“姿仪万方”,非陈清扬不能担起。
其实陈清扬很懂得与这个世界和谐共处,王二则相对鲁莽意气,但一样的是,他们最反抗最意气的一段日子就是在云南的那几年,所以当数年后相见,不止王二说那是他的黄金时代,陈清扬也说那是她的黄金时代。
“到潮退时我也安息,但潮兴时要乘兴而舞。”少年意气总有被磨平的时候,王二陈清扬也不例外。但至少他们曾经鲜活过。
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少年意气,敢于尝试,敢于说不,还没有向命运屈服的此刻,也恰巧就是永远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