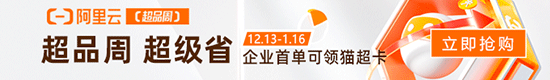国立武汉大学 国立武汉大学谁提的字
1933年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1次临时会议讨论决定,特任王世杰为教育部部长。同日,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电汉催促王世杰来京接事,至所遗武汉大学校长职务,决任该校教务王星拱担任”。
4月21日,教育部致电国立武汉大学:“该校王校长业经中政会决议改任教育部部长,已由本部电派该校理学院王院长为代理校长,仰即知照。”
4月24日,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总理纪念周”上对全校师生发表了离任讲话,高度评价“抚五先生忠诚劳苦,尤为全校所共仰。校事得抚五先生主持,当能平稳发展。这是兄弟的绝大安慰”。(注:王星拱,字抚五)
4月2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98次会议决议通过了由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出的“请简派王星拱为武汉大学代理校长案”。同日,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主持召开第9次临时校务会议,会上报告了“教育部电知行政院议决派本校理学院王院长代理本校校长”,并决定改推皮宗石和查谦分别出任王星拱原本兼任的教务长与理学院院长之职。
5月1日,王星拱首次以代理校长身份在“总理纪念周”上作报告。同日,王世杰离开武汉大学,于晚间乘轮前往南京就职。
以下内容,系拙著《功盖珞嘉 “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章《创建武大 主持校政(1928-1934)》第三节《从代理校长到校长》的书摘(对其中的注释略有修改),笔者当年所能搜集到的史料可不像今天这么丰富,衷心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对自己早年的这部略显稚嫩的专著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修订吧!
三、从代理校长到校长
(一)牺牲学术 全心奉献
王星拱作为国立武汉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从1928年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理工学院院长、评议员,到1929年担任理学院院长、代理校长、副校长,再到1930年的教务长、化学系主任及1931年的聘任委员会委员长,加上其它各种各样的大量兼职,可以说是全程参与了国立武汉大学从草创到早期发展几乎所有领域的校务工作,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所新兴的国立大学从诞生到一步步成长壮大的全过程,而他自己也成为了这所学校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导人物。
在多个重要职位上的繁重的教育行政工作,也不可避免地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令其难以兼顾,无法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投入足够的精力。王星拱本是一位出色的化学家和哲学家,也是较早在国内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的先驱。1917-192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王星拱在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不仅先后出版了专著《科学方法论》和译著《哲学中的科学方法论》,还时有多篇关于化学、生物学、哲学、宗教学、科学概论甚至社会科学方面的各类论文、评论或学术演讲录发表于各类报刊上。但自从他1928年来到国立武汉大学工作后,除了1930年9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科学概论》一书,以及1932年12月在《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第3卷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细胞及体素之通透问题》之外,此后便再无任何学术专著及专业论文问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名优秀的学者若是全身心地投入于教育行政工作,将会给他自身的学术研究事业带来多大的冲击和影响。
对于这一点,王星拱自己也深感不安,在1929年6月被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聘为副校长之后,王星拱曾公开向全校师生表示:
兄弟个人因为王校长的劝勉,现在勉强担任副校长的职务了。兄弟素无事务才,对于这个职务,实在是不敢轻于担任。而且兄弟以为学问与事业是不能同时都有成就的,因为这两件事的兴趣是不同的。譬如说:有一个人正在用功读书的时候,忽然有一种事务来分他的心,结果必定是书是读不好,事也是做不好。教授是要读书,副校长是要做事;兄弟是愿意在读书方面尽力,对于做事方面,没有什么兴趣。不过现在学校基础尚未巩固的时候,王校长有许多对外的事情,要努力去进行,他要兄弟分工任事,兄弟也只得暂时勉强担任。到了开学以后,学校各种事务渐入于顺序发展的时期,兄弟还只负教授的责任。[1]
由此可见,王星拱对于学术研究与教育行政工作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他相信,由于这两件事的兴趣不同,性质各异,而一个人的精力又毕竟是有限的,故“学问与事业是不能同时都有成就的”,一旦有所分心,则“结果必定是书是读不好,事也是做不好”,故必须有所取舍。同时,他也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愿意在学术方面尽力,努力做好一名普通的教授,而不愿意在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都不足以胜任的副校长职位上耗费时日。但由于学校初创,基础未牢,很多繁重的行政事务需要不少专人负责处理,特别是王世杰校长经常要为落实学校的建筑经费以及疏通各种社会关系而长期出门在外,具体的校务工作更是需要有一位得力能员代为全面主持;又由于王星拱的个人资历与威望均令广大师生深为信服,也就成为了副校长、教务长等重要行政职务的最佳人选。
因此,虽然王星拱的个人兴趣和意愿更多地在于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方面,但为了神圣、崇高的教育事业,为了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大局”,他还是被迫在自己的学术兴趣与学术研究事业上作出了重大牺牲,将主要精力投入于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一步步地从代理校长、副校长、教务长的职位走向再度担任代理校长,并最终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二任正式校长。而这一步一旦迈出,便再无回头路可走。对此,不少武大化学系的学生后来也纷纷表示了惋惜之情,他们互相传言道:“抚五先生本是一位杰出的化学教授,可惜转业行政工作,反而掩盖了他的长才。”[2]1935年以后,王星拱便不再从事任何教学工作,但对于自己的化学研究事业,依然是恋恋不舍,并没有完全放弃。据1937-1941年间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外文系的著名散文家吴鲁芹[3](1918-1983)回忆,王星拱校长在“处理学校行政之外,还不忘他的本行,一星期中有几个下午是在实验室中做他的实验的”[4]。但也正是由于“处理学校行政”工作的紧密限制,使他在自己“本行”里的深入发展受到了根本的阻碍,也丧失了更多的机会。如在1937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曾指名资助王星拱前往英国研究一年,但当时已身为一校之长的王星拱,显然是不可能轻易弃校远行的,于是,他便将这一美差让给了时任化学系主任黄叔寅(1902-1961)教授,并另聘陶延桥教授代理系主任一职,从而再次主动放弃和牺牲了自己在专业发展上的一次绝好的机会。
(二)水到渠成 接长武大
1933年4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为教育部部长,并电派该校理学院院长王星拱为代理校长。于是,在时隔4年之后,王星拱再一次担任起代理校长的职务。所不同者,1929年的代理校长,是在原代理校长刘树杞辞职、而新任校长王世杰一时无法到任的情况下,由王星拱暂行代理校务,等到2个多月后王世杰到任之时,即自行解除职务;而1933年的代理校长,是在王世杰校长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之后,王星拱即开始以代理校长的身份全面接长武大,在平稳地度过了一年的“过渡期”之后,即被任命为正式校长,也是国立武汉大学历史上的第二任校长。
据王世杰1939年在重庆时回忆:“六年前余离武汉大学时,原拟推荐周鲠生继任,皮皓白以王为教务长,周为教授,谓宜推荐王抚五,予不得已允之。”[5]王世杰与周鲠生在早年留学英国时便已相识,后又先后获得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间都曾参加过巴黎的中国工人和留学生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运动,回国后又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共事多年,分别担任法律系和政治系主任。相近的学科专业背景与社会工作经历,使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王世杰拟推荐周鲠生接任校长之职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周鲠生当时仅为政治系主任,若遽然升格为校长,恐一时难以服众。因此,时任法学院院长皮宗石从大局出发,主张由行政地位较周鲠生更高的王星拱接任校长,毕竟,王星拱作为教务长,本身已是仅次于校长的全校第二号领导人,由他来继任校长,方才显得更为顺理成章,令人信服。于是,王世杰最终还是采纳了皮宗石的建议,改推王星拱为校长。
尽管如此,王世杰仍然对王星拱某些性格上的弱点心存疑虑,在他看来,“抚五为人太和缓,寡决断”[6],“抚五为人甚好,然优柔寡断,胸襟亦不豁达,此其短也”[7]。而长期与王星拱共事的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主任(后任文学院院长)高翰教授则认为,王星拱“待人接物,恳切诚挚。个人生活,简单朴素。他治学态度,十分谨严。常识尤其丰富。但性格上却倔强而有脾气,常常择善而固执之。不过,这种固执,是对事而非对人。也因此而使得很多人认为他乃是学者典范,而非治事长才。人本来谁都有弱点,抚五先生这种性格上的弱点,也可说就是他作人有原则的长处”[8]。王世杰与高翰对王星拱的看法尤其是对其“弱点”的分析,虽不尽相同,但对于王星拱的为人,二人的基本判断并无二致,一个说他“为人甚好”,一个说他“待人接物,恳切诚挚”,这表明王星拱至少在人品方面是没有什么争议、令人无可挑剔的。至于他的某些弱点和短处,无论是“太和缓”、“优柔寡断,胸襟亦不豁达”也好,抑或是“倔强而有脾气”、“择善而固执之”也罢,这固然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具体效能,但从根本上来说,亦是“瑕不掩瑜”,丝毫无损于其人格的光辉,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抛开个人品质、性格等因素不论,仅就从事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资历、经验及个人能力而言,王星拱此时全面接长武汉大学的校务工作,应该说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件。首先,王星拱既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较为深入地接触和了解过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和科学知识,可谓“学贯中西”;他既是优秀的化学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高等学府获得过硕士学位,又在科学普及事业及哲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并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里有着广泛的涉猎,已完全突破了学科壁垒,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各种不同门类的现代科学各自的专业特点和发展趋势,真正做到了“沟通文理”。而较高的学术水平与开阔的学术视野,正是一名大学校长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
其次,王星拱还具备了丰富的高等教育管理经验。此前,他曾在民国初年的全国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任教十年,担任过评议员、化学系主任、组织委员会委员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仪器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积极参与过北京大学的多种制度创设与校务行政工作,对北大的革新和发展贡献良多;又曾担任过第四中山大学区高等教育部部长,管理过江苏全省的高等教育;作为国立武汉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这所新兴的高等学府已工作五年,担任过多种要职,为武大的创办和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对武大各方面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和熟悉;甚至在武汉大学副校长的任职期内,还兼任过安徽大学的校长,在大部分时间都无法到校任事,而只能在数百公里之外的另一所高校进行“遥领”的情况下,也仍然通过合理的人事安排与制度建设,保证了安徽大学的各项校务工作均能井井有条地正常运作,为自己家乡新建的这所省立大学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王星拱已完全具备“独当一面”的卓越领导才能。
仅就王星拱1928-1933年在武大工作的五年经历而言,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理工学院筹备主任,他参与了所在学校和学院从酝酿到正式诞生的具体创办过程;作为评议员和校务会议的重要成员,他参与和主持过多次评议会和校务会议,从而参与了武大多项规章制度的制订与修改及众多重大校务事项的决策与处理工作;作为一度的代理校长、副校长和教务长,他全面地代理过校长的职务,或是直接协助校长处理过众多事关全局的校务行政工作;作为理工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和化学系主任,他直接推进了自己所在学院、学系的学科发展和建设;作为教务长、课程委员会委员、预科算学委员会委员长、基本英文课程委员会主席、考试委员会委员,他对教学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日渐熟练与精通;作为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图书委员会委员、仪器委员会主席(委员长)、财务委员会委员以及特别(种)基金保管委员会委员长,他在筹措和支配、管理办学经费,推进校舍建设,购置图书、仪器设备等办学资源各方面均有不小的贡献;作为聘任委员会委员长,他也严格把关,为学校招揽了不少优秀的教学科研人才……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身兼多种要职,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充分历练,不断摸索、积累经验,这使得王星拱迅速了解和熟悉了学校教育行政事务的方方面面,也使其对大学管理工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宏观上的整体认识和全局性的掌控能力,为他日后逐渐走上全面接长一所新兴国立大学的领导职位,作好了充足的准备。另一方面,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能够在如此众多的工作领域里,为武大的发展作出过如此全面而重要的贡献的,恐怕全武大也很难找出第二人了。即使是在王世杰担任武大校长期间,由于他经常需要离校去处理各种校外事务,校内的绝大多数事务也多是由王星拱代为处理的;因此,到了王世杰行将离任之际,王星拱作为他最为得力的助手,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继任校长的最佳人选。
从客观条件来看,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在其四年任期内的卓越成就,也已经为他的继任者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周鲠生1947年10月31日在国立武汉大学第十九周年校庆暨三十六年度开学典礼上的报告所言,武大改建之初,在李四光先生“首先提议以一百五十万元巨款于武昌郊外另建新校舍,改造环境”之后,“真正实现李四光先生的理想而创立本校规模的,则是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先生”,王世杰校长“于民十八年由京辞官来主校政,当时学校尚在东厂口,珞珈山新校址圈地手续尚未办了,而所谓新校舍之建筑费一百二十五万[9]中,实际领到的只有二十万元,加以省政府已改变,情势变迁,一切都有落空之象。王先生在最困难的时期就职,不到一年,珞珈山新校舍工程居然开始,再过两年武汉大学居然迁到珞珈山新校舍授课了。及至民二十二年王先生因被任为教育部长离开学校,本校建筑设备以及制度人事都已树立规模,我们继任的人、至今大部犹可说是萧规曹随。他对本校创建的伟大功绩,真是不可磨灭的”。[10]
诚如周鲠生所言,在王世杰的四年校长任期内,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已基本走上正轨,因此,作为后继者,只需做到“萧规曹随”,沿着王世杰等人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即可,而完全没有必要对学校的各项制度及人事进行较大的变动。此时此刻,以王星拱丰富的教育经验和稳健的个人能力而言,加以其沉稳、和缓而又固执的性格特征,可谓完全符合“萧规曹随”的基本要求,作为王世杰所开创事业的继承者和守成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诚如1941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的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严耕望(1916-1996)后来所言,“雪公校长是一位有气魄有冲劲的创业长才,而抚公校长则是一位善于守成的良才”[11]。有王星拱这位“守成的良才”来打理校务,武汉大学的发展必定能保持蒸蒸日上的强劲势头,至少不至于被断送,王世杰大可放心地晋京赴任。
1933年4月24日,刚刚被任命为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校长,在“总理纪念周”上向全校师生发表了离任讲话,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一方面,他“感觉非常难过。如果接受这个职务,不但与本人素愿相违,而且对不住本校同事与同学……应该做而没有做,打算做而没有做的事体如此之多,此时如果走开,不与本校同人共同努力,私衷自极难过”;但另一方面,“如果兄弟对于这个职务绝对拒绝,许多朋友,又以为值此整个政局异常危险的时候,任何人都应该鼓起勇气冲入困难的环境中去苦斗,不应该规避畏缩……如果完全拒绝,许多人必认为本人畏难苟安,对于本校以外的事业,缺乏同情心”。因此,这种矛盾的心情,使他“感觉得十分不安”,但值得欣慰的是,“好在政府已决定请王抚五先生主持校务;各位院长各位先生也一致表示,愿对本校未来的发展,竭力负责”。说到这里,王世杰又不吝言辞,在全校师生面前将王星拱数年来的辛勤劳作进行了高度的称赞和肯定:
近四五年来,抚五先生暨各位教职员先生,对于校务发展,均竭知尽能,不辞劳苦。抚五先生忠诚劳苦,尤为全校所共仰。校事得抚五先生主持,当能平稳发展。这是兄弟的绝大安慰。因此,上星期末,兄弟已电复行政院,应允于短期间内勉强担任教育部的职务。[12]
4月25日,国立武汉大学召开第9次临时校务会议,确定了王星拱出任代理校长之后,与之有关的几个重要职务的人事安排与变动——其原有教务长一职,改推原法学院院长皮宗石担任;原有理学院院长一职,改推查谦教授代理;而皮宗石所腾出的法学院院长一职,则由原商学系主任杨端六(1887-1966)教授代理。[13]从此,皮宗石、查谦、杨端六等人便开始成为王星拱的得力助手。
(三)平稳过渡 代理“扶正”
第二次出任代理校长,王星拱的心态可以说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在王世杰于5月1日离开武汉,赴南京就任教育部长之职的同时,王星拱在“总理纪念周”上向全校师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首先指出:“现在校长往中央去,是学校重大的损失。虽然是暂时的,但是这个损失还是很重大的”,而武大师生之所以“要经受这样重大的损失”,主要是因为要“牺牲局部的利益,救济全部的利益”——为了更好地整理和维持全国的教育事业,为了改善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出于王世杰校长与中央政府各界人士的私人友谊起见,“我们不能不让校长到中央去”。而对于自己出任代理校长的职责,王星拱则小心翼翼地表示:
至于校长离校之时,本校的校长职务,叫兄弟暂时代理。兄弟材具不够,身体也不好,本不敢担任,但是过于顾虑,又恐怕对不住朋友。好在本校的进行,是由校长和各位先生原定有确定的程序,——如图书馆法学院之建筑,机械序[系]之设置,研究所农学院之准备,以及一切充实内容之计划,——现在我们还是照着这个程序去进行。我们同校长说过:将来到了中央政局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须得请校长回来。或者是到了中央完全无办法的时候,我们也须得请校长回来。还有一层,兄弟在代理的时间,自然是竭尽能力和诸位先生共同负责照原定的程序往前进行。但是到了无力前进的时候,兄弟决不因循敷衍而阻止学校的进步。到了那个时候,还得要校长提早回来,免得把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校,因为代理失职而停顿了。[14]
尽管王星拱处处言辞谦虚,谨小慎微,但他在第二次担任代理校长期间的实际表现,显然无负于他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从1933年5月开始的一年间,武汉大学的各项校务工作按照既定的计划和轨迹继续向前推进,真正实现了王世杰所期待的“平稳发展”:
1933年6月,国立武汉大学第二届毕业生共112人顺利毕业;
7月,学校从武昌、南京、上海三地招考录取新生共171名;
8月,总图书馆建筑工程开工;
9月,成立农学院筹备处,由代理校长王星拱亲自兼任筹备处主任,同时,工学院增设机械工程学系;
10月,学校将普通体育改为必修课,并举行毕业考试补考;
11月,代理校长王星拱重新聘定了全校各学系系主任;
12月,湖北省政府委托学校设置水利讲座并补助经费;
1934年3月,湖北省政府开始自1月起按月补助武汉大学建筑设备费2000元,汉口市党部委托武汉大学设置奖学金名额3名;
4月,已故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之子黎绍基、黎绍业兄弟将其先父筹设江汉大学之基金约10万元全部移捐给武汉大学,学校将其用于修筑体育馆之用;
5月,学校同时举行第5次春季运动会与第2次美术展览会;[15]
……
总之,在王星拱第二次代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的一年时间里,学校在校舍建设、设备添置、经费筹措、学科发展、科学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平稳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功业既昭著如此,其校长之职由“代理”到“扶正”也就为期不远了。
1934年5月1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作出决议,正式任命王星拱为国立武汉大学第二任校长。[16]
[1]《本大学第二十五次总理纪念周纪录》(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27期,1929年6月24日,第2版。
[2]殷正慈:《我所知道的王抚五先生》,董鼐总编辑:《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59页。
[3]本名吴鸿藻,字鲁芹,后以字行。
[4]吴鲁芹:《我的“误人”与“误己”生活》,台湾《传记文学》第26卷第2期,1975年2月,第37页。
[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民国二十八年一月~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90年,第75页。
[6]《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42页。
[7]《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75页。
[8]殷正慈:《高公翰先生谈文学院》,《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第37页。
[9]此处应为“一百五十万元”之误。
[10]以上引文参见《本校第十九周年校庆暨三十六年度开学典礼校长报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374期,1947年11月1日,第1-2版。
[11]严耕望:《我与两位王校长》,《学府纪闻·国立武汉大学》,第71页。
[12]以上引文参见《上周纪念周王校长报告词》,《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63期,1933年5月1日,第1版。
[13]《国立武汉大学校务会议纪录》第4册,第147-148页,武汉大学档案馆藏国立武汉大学档案,档号6L71932JX023。
[14]以上引文参见《上周纪念周王代校长报告词》,《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64期,1933年5月8日,第1版。
[15]以上内容主要参见《沿革概要》,《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华民国廿三年度),第8-10页。
[16]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3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84年,第368页。
相关阅读:
技术帖|武汉大学历任校长考
功盖珞嘉“一代完人”——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