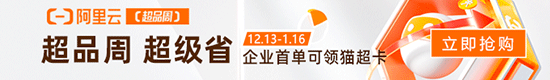折戟沉沙铁未销 折戟沉沙全部小说
建筑是一门艺术,且总是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以下是人们熟知的:黄鹤楼与崔颢的七律《黄鹤楼》、鹳雀楼与王之涣的五绝《登鹳雀楼》、滕王阁与王勃的《滕王阁序》、岳阳楼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一一对应,难分难解。外国也有类似的情形,两年前巴黎圣母院被一把火烧得惨不忍睹,于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立即成为抢手货,人们在震惊之余急于重温这部经典之作。
也有一些著名建筑联系着一批文学作品而难举出最知名之作的,例如邺城(今河北临漳)的铜雀(或写为“爵”)台。
铜雀台是曹操(155—220)把政治中心安置在邺城以后大兴土木建的建筑成果,规模宏伟,气势不凡。《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张载注云:“铜爵园西有三台,中央有铜爵台,南则金虎台,北则冰井台;有屋一百一间;金虎台有屋一百九间;冰井台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三台与法殿皆阁道相通,直行为径,周行为营。”铜爵台虽然不是最大,但在三台中最重要,知名度也最高。
邺城遗址
青石角螭首(1986年西铜雀台遗址出土)
涉及铜雀台的作品甚多,最为读者熟悉并且很容易记住的,也许是晚唐诗人杜牧(803—852)的那首《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赤壁之战以南方获胜、曹操大败而告结束,孙权刘备方面在年轻的前敌总指挥周瑜领导下顺风放火,烧得不大习惯水战的曹军焦头烂额,狼狈逃窜。就此歌颂周郎的文学作品甚多,而对军事学大有兴趣的诗人杜牧却认为南方赢得有点侥幸,尽管战术安排上万事俱备,然而,如果不刮东南风,胜负就会颠倒过来。万一颠倒,从大处说,此后的历史将是另外一种走向,而从小处来说,则江东两位美人——大小二乔,将成为曹操的战利品,深锁铜雀台中。
曹操喜欢美人、歌女,他的身边也一向有大量的歌妓。此事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以及裴松之的注中多有记载。咏史诗如果只就宏观立言,不容易出彩,总得有点好看的细节才好。杜牧是这一领域的高手,这里把铜雀台列出来,又把二乔推进去,诗味大出。
咏史诗里的细节,有时是经不起深究的,查赤壁之战在建安十三年(208),而铜雀台要到建安十五年(210)冬天才开始兴建,十七年(212)春落成。即使曹操能把二乔掳去,也须先在别处安置,稍后才能辗转调入铜雀台中。
如果对杜牧去讲这些时间和地点的元素,那就是措大式考证,将一举杀尽诗中的情趣。在诗人笔下,历史是一段故事,可以推测,可以重塑;历史又是一枚钉子,足供诗人把他的感慨、情绪、见识、议论统统挂于其下,这才能赏心悦目,提供启示。
建安十七年铜雀台落成之初,曹操兴奋地带着群下和他儿子们一起登台,率先亲自作赋一篇,可惜现在只能看到两句。《水经注》卷十载:
魏武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入,迳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渠水又南,迳止车门下。魏武封于邺,为北宫,宫有文昌殿。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窦下,故魏武《登台赋》曰:“引长明,灌街里”,谓此渠也。曹操又命令他的文学家儿子作赋,于是曹丕(187—226)、曹植(192—232)各写了一篇。“(曹)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曹操)甚异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曹植传》)。曹植高调地写道:
从明后而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
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川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
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
虽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
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曹植对铜雀台及其周遭景物只作大笔勾勒,很快就转入抒怀,全力歌颂老爸的丰功伟绩,说是比齐桓、晋文还要高出一头。这正合于曹操本人当时往往拿齐桓、晋文来自我标榜的基调(详见其《让县自明本志令》)。赋末以长寿为祝,更正对乃父心事。
登高能赋是古代十分重视的一项基本修养。《三国志演义》里也曾写到曹植登铜雀台作赋、大出风头一事,但是未作正面描写,而是通过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夜初见周瑜时的一番说词带出来的。
诸葛亮说,现在大军压境,形势紧张,而要想让曹操退兵其实也非常容易,只要把大乔、小乔送过去就行了,曹操老贼率领大军南下,无非为此二人。对于是否要打这一仗尚存犹豫的周瑜听了颇为吃惊,忙问此说有何根据,诸葛亮说根据就在曹操之爱子曹植的《铜雀台赋》中,他立即背出该赋,其中有几句道:
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
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
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周瑜听罢大怒,诸葛亮劝他不必生气,“何惜民间二女乎?”周瑜说先生你有所不知,大乔是孙伯符(孙策)夫人,小乔乃瑜之妻也,“吾与老贼誓不两立!”于是不再犹豫,决心同曹操决一死战。
这一段生动有趣的对话见于小说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此时铜雀台连个草图都还未出炉,但这并不妨碍小说可以这么写,小说中的诸葛亮也可以为曹植的赋添加出这些句子来。
何况唐人杜牧早已说过:“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铜雀春深”这一句看来给了小说家很大的启发。
杜牧的《赤壁》言之有味,令人耳目一新,传诵甚广;但也遭到过严肃批评。宋朝人许顗指出:“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彦周诗话》)清朝人秦朝釪更直斥杜牧之诗“如吴门市上恶少年语,此等诗不作可也。”(《消寒诗话》)照他们的意思,诗中应写如欠东风则将危及社稷苍生,而绝不能谈什么女人。
如果按许、秦一派评论家的高见去写诗,议论固然正大,可惜诗味恐怕也就所剩不多了。何文焕说:“夫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之不保。彦周未免错会。”(《历代诗话考索》)贺贻孙《诗筏》说“诗家最忌直叙,若竟将彦周所谓社稷存亡生灵涂炭孙氏霸业不成等意在诗中道破,抑何浅而无味也。”
大小二乔进驻铜雀台,即是吴亡,如此则孙氏霸业落空、东南生灵涂炭等情自可不言而喻。何况“铜雀春深”言外还有对曹操的调侃之意,曹操乃是赤壁之战的另一方,打仗总得有敌我双方,写到曹操更合于诗题,也可以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
事实上铜雀台里确实多有美女,她们是为曹操表演歌舞的一批艺术家。曹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傅子》);他在遗嘱里还特地交代:“吾婕妤妓人,皆著铜爵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转引自《文选》卷六十陆机《吊魏武帝文》)。音乐方面的爱好死后也不能放弃,所以铜雀台上要给他准备好一个专门的席位,好让他每月欣赏女艺术家们的表演。
这种将欣赏音乐放在最优先位置的遗嘱真可谓前无古人。稍后陆机(261—303)从国家档案里亲眼看到过这份遗嘱,十分激动,在他那篇著名的《吊魏武帝文》中大发感慨道:
结遗情之婉娈,何命促而意长。
陈法服于帷座,陪窈窕于玉房。
宣备物于虚器,发哀音于旧倡。
矫戚容于赴节,掩零泪而荐觞。
……
徽清弦而独奏,进脯糒而谁尝?
悼繐帐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
登铜爵而群悲,眝美目其何望。曹操对他网罗而来的这些歌妓感情之深,有如此者。像曹操这样死而不已的音乐迷,才是真正的热爱艺术。
文学家们写铜雀台,起先大抵是注意描写这里的环境和建筑,三曹的铜雀台赋和左思的《魏都赋》都是如此。辞赋的传统,本来就重在“体物”。可是后来到中古后期,曹操的遗嘱已经被公开,让人们大开眼界,于是诗人们再写铜雀台这个题目就往往抛开这里雄伟壮丽的建筑不谈,而专门就曹操与他安排在铜雀台里的歌妓来抒情——这时通行的新传统是“诗缘情”了。
曹操与歌妓们的感情联系,乃是齐梁时代的诗人们关注的热点,这样的诗篇往往径以《铜雀妓》为题,可试举几首——
武王去金阁,英威长寂寞。雄剑顿无光,杂佩亦销铄。秋至明月圆,风伤白露落。清夜何湛湛,孤烛映兰幕。(江淹)
繐帐飘井幹,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詎闻歌吹声。芳襟染泪迹,婵娟空复情。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谢朓)
秋风木叶落,萧瑟管弦清。望陵歌对酒,向帐舞空城。寂寂庭宇旷,飘飘帷缦轻。曲终相顾起,日暮松柏声。(何逊)
雀台三五日,歌吹似佳期。定对西陵晚,松风飘素帷。危弦断更续,心伤于此时。何言留客袂,翻掩望陵悲。(刘孝绰)
这些齐梁诗人都没有到过邺城,他们对铜雀台的描写皆出于想象,歌妓同曹操之间有一种艺术家与知音的心心相印,也颇有微妙的情愫。齐梁时代最喜欢描写两性情感的诗人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客体。
西陵、繐帐、管弦、歌吹、松风等等,从此成了铜雀台这一题材的常用关键词,由此不难拼凑成文,所以以《铜雀妓》为题的诗歌缺少特别优秀、特别令人难忘的篇什。
稍后由南而北的诗人荀仲举也写了一篇抒情的《铜雀台》诗,重点仍在铜雀妓:
高台秋色晚,直望已凄然。况复归风便,松声入管弦。泪逐梁尘下,心随团扇捐。谁堪三五夜,空对月光圆。
此诗原载《文苑英华》(卷240)和《乐府诗集》(卷31),后者列入相和歌辞之平调曲,应该是可以入乐的。荀仲举这首诗描写铜雀妓们对主公曹操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现在的眼泪和悲怆。
同江淹、谢眺、何逊、刘孝绰等人不同,荀仲举亲自到了邺城,是看到过铜雀台风光的。他作为战俘由南而北,虽然北齐官方对他相当客气,但他远离家乡,总不免有些感伤(详见《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传》中有关荀仲举的部分),所以诗中有“直望已凄然”这样的诗句。他在三五(每月的十五)之夜泪流满面,恐怕乃是乡愁的表现,不过借着铜雀妓来自抒其情罢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历来是诗人抒情的常规之一。可惜荀仲举的诗现在只能看到《铜雀台》这一首。
由于历史的惯性,铜雀妓这一题材在唐朝仍然方兴未艾,高适(700?—765)就曾写过一首: 日暮铜雀迥,秋深玉座清。萧森松柏望,委郁绮罗情。君恩不再得,妾舞为谁轻?
邺城在唐代改名为相州,诗人高适在开元二十七、八年间(739、740)来游相州,诗当作于此时。高适此诗同历来的同题之作一样,着眼点在于咏叹那些歌舞妓对曹操的知遇之感,诗中的“玉座”指曹操为自己安排的有繐帐的八尺床,“深”则是说其座虽近,而其人已远;遥望西陵,这位英雄的坟墓上松柏萧森。既已天人远隔,还有什么情绪轻盈起舞,重唱当年那些老歌呢。
在这首诗里,曹操还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这也是历来以《铜雀妓》为题诸作的基调,此后欧阳詹(757—802)的同题之作有云:“萧条登古台,回首黄金屋。落叶不归林,高陵永为谷。妆容徒自丽,舞态阅谁目。惆怅繐帷前,歌声苦于哭。”在这首诗里,铜雀台歌妓们对曹操的感情仍然未变。
到宋代以后,就不大有人再写铜雀妓这个题目了。曹操本人的形象日甚一日地走向反面,变成奸雄,对他怀有一片深情的歌舞艺术家也就退出了诗坛。就是先前的各首《铜雀妓》也渐渐落入边缘,不复为读者所重了。
一般来说,怎么写远比写什么重要,但题材也颇有关系,在传播方面影响尤大,如果题材不合后人的口味,往往就很难进入经典。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者:顾农
编辑:于颖